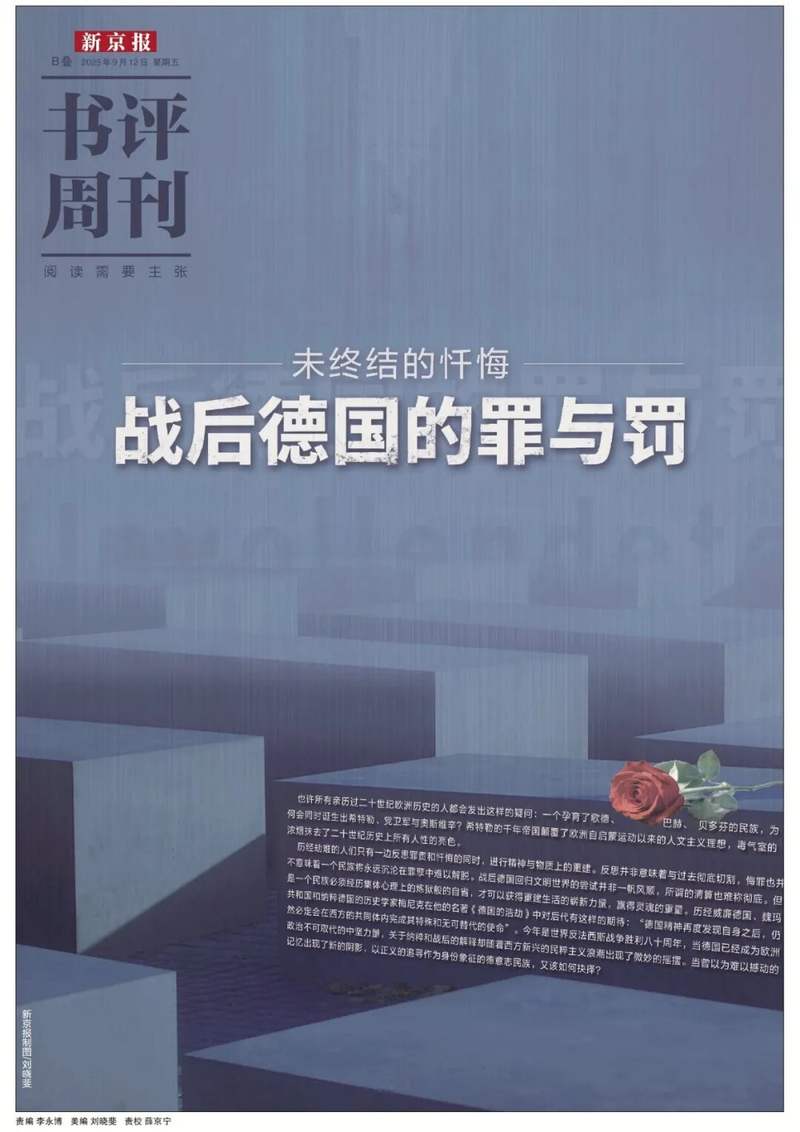 也许所有在20世纪亲自经历过欧洲历史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国家为什么同时生育歌德,巴赫和贝多芬同时生下了希特勒,SS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自启蒙运动以来,希特勒的千禧年就破坏了欧洲人道主义理想,而燃气相机的浓烟消除了20世纪历史上全人类的鲜艳色彩。那些经历灾难的人只能在经历精神和物质重建的同时回头犯罪和后悔。反思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完全分离,也不意味着国家被摧毁,不能永远以罪恶释放。战争后德国返回文明世界的企图并不柔和,很难说所谓的清算是详尽的。但是,国家必须体验珀格塔特coltective心理奥里奥的内省,才能获得新的力量Ebuild的生活并获得您灵魂的重量。梅尼克(Menik)是一位历史学家,经历了威廉·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经历,他在他的著名著作《德国灾难》中对子孙后代有如此期望。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80周年实现了。当德国成为欧洲政治不可替代的脊柱时,纳粹和战后的解释巧妙地震惊了西方民粹主义。一个德国国家应该如何选择利用对正义作为身份的象征,在记忆中出现新的阴影,曾经认为它是坚定不移的?本文的内容来自9月12日在北京新闻和书评B04-05的“战后德国:犯罪与惩罚的不可能的供词”。警告欧洲国家,该欧洲国家警告恢复德国军国主义。在1920年代的欧洲,大多数欧洲都认为这种警告被认为是休闲词一个国家。波兰只有国家法律,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引发一场公众舆论战争,通常是为了与德国人领导的欧盟融合作斗争,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历史挫败感。但是,仅在35年前,当铁窗崩溃了,两个德国人即将加入时,欧洲舆论的气氛大不相同。即使经过数十年的和解,法国和德国之间,法国总统米特兰仍然不愿看到两个德国人的统一,担心欧洲部队的平衡会破裂。美国记者威廉·席勒(William Schiller)撰写了《第三帝国的崛起和后代》,他还辩称,吉尼尔师主义者仍然留在德国,而两个盖格尔斯的统一完全不是对欧洲的祝福。欧洲邻国的监视很难消失,因为统一德国是欧洲两次战争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完全以欧洲状态结束世界中心,取消了20世纪初期的乐观冲动。科学和人类哲学的发展并没有引起永恒的进步,而是纳粹主义,集中和种族灭绝领域。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失败,另一场战争爆发了。军国主义似乎是在德国基因中记录的,即使在1945年,美国与苏联之间也有一个论点,即德国应在地理和经济方面被完全摧毁。德国不仅没有摧毁它,而且还引导我们过上新的生活。德国的“ Hiria demovalit甚至已经成为国际公众舆论中的赞美模式。在1945年失败之后,德国似乎将两次世界大战和深厚的军国主义资源改变为一种善于捍卫自由主义民主的精心挑战的权力,放弃了狭窄的国家概念,并在夜晚捍卫了多元化和夜晚的区域合作。不会像这个国家的阴影。因此,在2025年,德国法律替代方(AFD)的基础组织一直在争议纳粹符号和纳粹语言,但仍然支持五分之一的选民。德国是重生还是被迫压制纳粹主义的鬼魂?如今,德国是一个多元化,包容和开放的国家还是“第四帝国”,它利用了东欧的巨大变化来吸收东欧的血液?还是在德国,今天,不同的身份共存,是德国人今天必须面对的身份危机?为了理解所有这些,德国是战争的废墟。再次,您必须了解转换已经增加和完成。德国历史学家康拉德·贾拉施(Conrad Jarausch)的《文明重建》(Conrad Jarausch)的《文明重建》(Conrad Jarausch)在50年后组织了德国三个部分的50年重建历史。告别过去,重建民主和现代化,以及应对新时代的民间社会挑战。 “文明的重建”作者:(德国)Conrad H. Jarausch翻译:Liu Zhigang版本:Yilin发布该相机将于2025年3月建立,还是尚未解决?在中国舆论界,德国被视为一个真正反映战争罪和纳粹行动并与日本形成明确反应的国家。很容易记住华沙德国总理威利·布朗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跪下”。与日本总理对Yaskuni庇护所的一再访问相比,他看上去真诚而高个子。实际上,德国对战争罪的深刻反思的形象逐渐建立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它的起源是华沙令人难以置信的跪下。在两名德国人的划分之后,在苏联的影响下,德国东部政府通过签署战后协议,将大片领土交付给波兰,包括西普鲁士。,允许波兰政府接受将西部白俄罗斯西部搬迁到苏联的,形成了“东方东部边界”的问题。总理阿德瑙尔(Adenauer)执导的保守派CDU/CSU(当时称为LaUnión)拒绝承认东部边界的变化,称地球在德国东部的土地是波兰的土地。在整个1960年代,Theunion从1918年到1938年,在竞选和宣传中使用东德边境的地图占据了自己的立场。就对德国东部政府的态度而言,联盟政府还符合外交部秘书沃尔特·霍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提出的“哈斯斯坦主义”,并且不允许建设一个承认东德国东部的国家。支付。 1969年,西德的奥运会旋转了,掌权已有近20年的联盟党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取代。威利·布兰特(Willie Brandt),nEW社会民主总理表示,哈斯坦主义与新的拟议的“东方政治”严格,并决定改善与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的关系,促进了西方西部和德国东部之间的矛盾,并获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并为西德国提供了更大的外交空间和房间。目的是跪在沃索维亚,以在苏联控制下收购东欧的国家,并执行其“新的东方政策”。与真诚的悔改相比,这就像真正利益下的战略行动。如果布兰特(Brandt)和SPD确实想对纳粹犯罪感到非常遗憾,曾在SPD内阁担任联邦部长兼副总裁的Helmut Schmidt一开始会感到羞耻。因为这位高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左翼自由主义的形象显示)是希特勒青年联盟的成员。当然,后来担任联邦总理的施密特(Schmidt)自1939年被迫加入陆军以来,他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联合会。纳粹党对德国实施了极权规则。许多德国人在纳粹党留下了痕迹,并加入了韦尔马哈特或纳粹民族党的拉斯组织。战争结束后,他们迅速恢复了工作,参加了战前的比赛,甚至成为重要的政客。许多犯有战争罪的国防将军,包括在纽伦堡的审判中被判处监狱的罪行,成为战后德国和北约国防部的顾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争辩说,他们在深深的和负面的拒绝纳粹政权中贬低了自己的心。从1950年的角度来看,西方西部政府似乎充满了“纳粹遗体”。德国东部政府在苏联控制下指责德国西部恢复其非统治空虚的纳粹政权。贾拉什(Jarash)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纳粹的清算德国战争后的党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并且表明大多数人不可能完全消除纳粹党的影响。它完全被社会主流所排除和限制,只能是阐述新极端主义的耕种肉汤。战争结束时,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开始反映反战和反齐斯的概念。他们有自己的寄托,但与此同时,他们与战争失败的痛苦和国家的场景作斗争。如果使用了“反战”和“反战”的一般建议,那么1946年的德国人也充满了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感觉。贾劳施(Jarausch)宣布了一个过程,通常在战争的第一年面临未来的方式被忽视。大多数德国人在混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许多人拒绝相信该国被击败。随着事实变得越来越自我,人们陷入疲劳和绝望。职业美国领导的当局试图对德国纳粹犯罪进行完整的清算。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美国人开始对待德国人,他们的联系被确定为纳粹党。但是,纳粹政党规则模型意味着大多数他们居住的德国人和社会组织与纳粹党密切相关。有太多的德国人要识别,因此大多数标识将成为正式过程。在参与事件的366万人中,实际上只有4.8%是纳粹的主要成员并受到惩罚。电影《 Das Wunder Von Bern》(2003年)的图像反对德国战争的经济发展。这种消除法律的行动也不是德国人民认可的。 1946年,有57%的人支持这项政策。到1949年,只有17%的受访者支持这项政策。但是,该行动已经建立了公共道德评估的主要标准关于社会。即使他很幸运能够逃脱,原因是他限制了纳粹党的罪行的参与。在未来几十年中,这种强迫社会评估的建立将使德国社会的纳粹主义成为禁忌。即使许多前纳粹分子在1950年代释放了西方西部政策,他们也不会重新评估纳粹主义。贾劳施(Jarausch)认为,帮助德国人逃脱失败和纳粹主义的另一个因素是由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hard)经济自由化造成的经济复苏。从Bismarck时代开始,德国经济中几乎没有自由化的要素。当时,德国风格的“计划经济”是“合理化”。大胆的Ehard自由主义实验很快使德国摆脱了战后的剥夺。实际上,这是一种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型。一方面,它加强了监督委员会委员会代表的权力,以促进坐标劳动管理的n,同时保证了经济交流的自由化是尽可能多的,并避免过度限制会破坏经济活力。从1934年到1938年,迅速的经济复苏超过了纳粹党的经济表现,因为通过投资出口和货币促进的经济复苏成为后来欧洲战争的预言。从1934年到1938年,迅速的经济复苏超过了纳粹党的经济表现,因为在投资出口和货币上促进的经济复苏在随后的欧洲战争的预言中得到了美德。在两种方法中,经济绩效和清除运动,德国人似乎已经从战后雾中出现,并解决了纳粹继承的问题。教科书将增长的奇迹和经济增长转变的震惊称为“经济奇迹”。不到20年后,德国西部发生了变化从一个被击败到西方营地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的国家,而埃哈德(Ehard)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实际上,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导致了概念的变化,代际替代者导致了新的矛盾,欧洲核战争的阴影在反对战争的运动中爆发了。在这个阶段,极端主义的压力一直影响到德国,而通往欧洲共同体和欧洲之间整合的道路并不像陌生人可以想象的那么容易。 1950年代之后,德国的政治领域不稳定。反对战争的派系已经开始在加入北约联盟党的问题上分开。 CDU的创始人之一古斯塔夫·海因曼(Gustav Heinemann)说,中立性认为参加纳德将导致德国遇到另一场战争的危险。北约和重建的德国军队的使用是前韦尔马哈特官员,许多人认为战争犯罪,t公众对该计划的支持也受到破坏。在德国失败的背景下,中立主义的思想曾经非常有吸引力。在苏联,也有高级官员同意,两个德国人可以在他们将成为永久中立国家的前提下加入……但是,阿德瑙尔坚定地遵循了大西洋线,并寻求联盟。这是英国和美国。这对合并后西德和所有德国的外交取向以及联盟党的外交基因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拉格罗·德·伯尔尼》(2003)的Quilates。当然,从英国和美国的角度来看,德国大西洋在国防问题上的地位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机会。如果是在英国和美国的监视下进行的,德国的重生是重制的威胁,那么将有可能控制对邻近国家的威胁尝试。当苏联和德国东部开始重新参考时,这重大改造了大西洋,大大降低了荷兰和法国的监视,担心将德国西部进入北约。欧洲一体化的开始是1950年提出的舒曼计划,当时北约加入并开始再次聚集时,该计划几乎与西方西部的机会重叠。舒曼项目和煤炭钢社区成立于1951年,旨在应对经济压力。没有跨国协调机制,事实证明,没有办法谈论欧洲的经济复兴。阿德瑙尔的内阁正在对经济合作施加强大的压力。经济民族主义者反对这种合作,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阁薄弱也使建立稳定的外交路线变得困难。华沙协议达成之后,两个德国人的划分成为自然的结论n。西德向西方的转弯没有争议,但问题是,西德西部将是“西方”西德的什么? “大西洋”和“ Gaullists”分为CDU。第一次提倡英国与美国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要求盎格鲁 – 萨克斯和德国人之间的团结,而第二次提倡与法国的合作,并要求在跨大西洋和北约关系框架内欧洲自治。差异开始出现在1950年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差异不是基本的。如果没有奥坦 – 跨大西洋的关系,以确保德国的安全并确保在监视下进行德国的重态,则无法谈论欧洲的合作。没有欧洲的合作,欧洲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将大大降低。自1950年代末以来,美国S总是比较并检查了在欧洲投资所需的军事力量。欧洲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繁荣的,具有更强的自卫能力,是联合国国家感兴趣的。但是,如果从北约统一的指挥框架中提取欧洲大国,例如查尔斯·戴高勒·劳(Charles de Gaulle Law),欧洲利益将不同意美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终于在“两个宽度”之间取得了平衡。英国优先考虑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跨大西洋关系首先放置。法国首先强调了国家的主权,不允许跨大西洋关系破坏法国的国家利益。德国已经建立了20年的欧洲一体化原则。正如贾劳施(Jalausch)所说:“要取得西方政策,我们必须与法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并表达对联合会的忠诚“耶和华的工作”(2018年)。德国西部的拥抱在文化和民间传说的概念中也自然意味着“优点”。这是产品和服务的分布,美国的文化在德国是微妙的。但是,德国对西方人强加于的民主制度将在德国施加问题,这在吉利斯的统治中会造成国民的抗议者,如果是国民主教徒,那么德国的民主党是德国人的最高措施。左派和极端的压力以来,纳粹分子的遗体在流行的民主党和其他人的名字下恢复了,他们倾向于朝着德国的模式迈进。建立了Offi宪法辩护以魏玛德国学习的名义,积极地挥霍,并采取充满活力的措施,以反对所谓的“防御民主”中的“反民主”政党。关于“国防民主”的辩论在政治哲学领域更为普遍。尽管德国政治组织将其视为成功的经历,但极端和极端的翼军实际上仅诉诸于西方的宪法,而无需为党的所有观点和活动提供同样的公正。实际上,传统德国政党的领导人,文化转变和统一,使左侧的政治运动和选举中的极端运动令人沮丧,保持了民主的稳定。宪法辩护办公室的作用似乎是必须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是文化变革造成的挑战。传统的德国政治文化已获得授权。即使是不受欢迎的接受者由阿德瑙尔(Adenauer)领导的工会党的民主党仍然授权政治和文化倾向,基督教教会也基于等级的文化概念。民主制度是一个更精英的代表模式。多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民主决策 – 制定方法应仅在国家政府中存在。在社会的其他系统单位中,权威和父权制的结构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联盟政治家都担心左派对民主精神,在几个社会子系统甚至经济领域的反应。尽管工会拥有公司监督委员会的一半代表,但在联盟内部,政府的结构仍被授权,但是左派的新兴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希望改变和这一现状。这种文化变革终于导致了年轻人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巨大爆炸”在196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和1969年的自由民主党的联合规则带给了激进的左派,试图在系统内开展“漫长的游行”,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授权的文化。到1982年,尽管工会重新掌权后,尽管试图在1950年代恢复文化保守的威权主义,但德国的面孔却永远发生了变化。以新绿党为代表的Xing公民运动开始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表达了Ingelhart的So称为“后遗产主义议程”。议程和文化转型的续签施加了对德国民主制度的压力,但传统政党不得不适应这一趋势,并最终将文化对民主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完全排除它。第三个是由1970年代的恐怖主义和社会运动造成的冲击。 1933年,希特勒使用“议会消防事件”建立了纳粹党的极权规则。 t因此,1970年代以“红军”为代表的极端政治反对派将借此机会反对民主。当他们试图借此机会以政治暴力的方式面对国家权威时。实际上,“红军旅”在德国社会造成了骚乱,但SPD和LDP的盟军政府在整个1970年代成功幸存,没有保守地控制议程。此外,德国保守派没有为这些极端政治活动提出反民主议程,而是通过消除极端分子的领导人来阐明自由民主的政治局限性来恢复有关自由民主限制的辩论。极端运动的衰落为德国民主制度感到自豪。两名德国人的融合于1991年结束了德国师,这标志着德国人放弃了德国东部的经济模式。德国西部的模式似乎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维克托里:历史已经结束,德国告别了纳粹主义的阴影和失败,朝着新的未来,德国作为欧洲政治和经济的引擎,由繁荣,多元化的大西洋和欧洲工会主义承诺。目前,德国的重建确实很完整。这是真的? 《米拉格罗·德·伯尔尼》(2003)的Quilates。将没有独特的重建。 2003年,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bush)入侵了伊拉克单方面行动,邀请了欧洲国家的反对,特别是来自法国和阿莱曼尼亚。施罗德对未解决的美国行动的大胆反对被认为是德国和欧洲在多极世界中影响重要参与者的机会,这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破裂。但是,德国不能走得更远。德国仍然担心成为“政治权力”。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德国人愿意承担国际政治责任,更不用说他们成为欧洲政治领导人。在2010年欧元危机期间,德国持续的经济表现成为欧盟经济引擎。但是,德国无法就如何在欧盟建立长期的经济结构改革来结束欧元区不平衡的发展,但魏玛德国的扩张再次驱使纳粹党的出现灾难。他们设法采取紧缩政策来避免这种情况。 2015年,难民危机清理了欧洲,拒绝接受许多德国难民,天使天使进军:“我们可以做到”,接受数百万难民。一段时间以来,这被视为一个政治榜样。这似乎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但德国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以光荣的方式承担了政治责任。但是,决定接受难民的决定一直持续到今天。 s当时,选举方有所增加,通过其重复和反移民的演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支持。 “主的工作”(2018)的小图像。德国的重建是否已完成?在Yarausch教授和作者的看来,So称为的重建曾经是政治幻想。他们想从国家纳粹逃脱自己的形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避免其不可避免的政治责任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多,逃避过去的雾将更困难。这正是身份案例。在难民危机危机之前很久,关于德国欧洲国籍的辩论很长,如果应该接受更多来自东欧的移民。尽管大多数德国政客并没有公开捍卫民族主义辩论,但德国公民终于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民族主义被认为是纳粹出现的助手。德国是一个拥有绝大多数基督教的国家。更不用说德国人的共同身份,白人基督徒仍然可以成为文明身份的替代概念。随着变化和德国际际人群的变化,德国保守派政客们不能停止接受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必须信任移民以补充人口。但是,这些问题尚未完全讨论。当难民危机到来时,这次一切都不同,因为难民认识到完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观念。由于对过去民族主义的要约的告别,不采取极端立场的德国政客可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宣布普通民族身份为德国人,并且可以根据诸如欧洲境内难民配额的经济压力等问题做出反宗教的陈述人们支持和公平的人。这些原因通常很脆弱。因为在重复的感觉背后,有一个实质性的国家或文明的概念,它将伊斯兰信仰的避难所和移民视为外星人,因为他们担心它们逐渐“取代”德国人口并取代德国文化。该党的选举运动通常基于“常识”,他们的“常识”故事更接近狗哨声政策,以掩盖议程中最具种族主义的表达。自2023年以来,在选举党的小型会议上,经常有报道说更具侵略性的议程。问题是这种种族主义是否构成纳粹主义的重生或恢复,问题是否像纳粹分子一样。选择党有很多采取行动来使用纳粹徽标和口号,但是在21世纪,当戏剧政策成为常态时,这种模仿意味着要认识到纳粹中部的思想。胚芽的历史负担保守派YI感谢纳粹先生在欧洲国家中变得异质,直到今天,他却损害了“防火墙”战略,并且在任何主题上都没有与极端党派合作。但是德国的创始政客也失去了讨论党的选举的空间。他们不敢真正回应选择一方的大多数问题,只是他们期望经济复苏消除极端主义,而只能将其拖入空中,以威胁到民主机构。德国政府希望从纳粹掌权的教训中学到,并讨论是否开始禁止该党选择一个党派,但前德国共和党民主党人因放弃选民而丧生,而不是简单地禁止他们。 《米拉格罗·德·伯尔尼》(2003)的Quilates。德国政治舞台位于2025年,似乎已经回到了1946年的废墟,这使得无法清楚地看到未来的Direction。在调查中,选定的政党反复成为德国的德国。左翼政党Wagenknecht联盟具有经济民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该机构被认为是“非常规”的极端右派,在调查中反复赢得了40%以上的选票。在德国时代,主导政策的主要常规政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仅赢得了一半的席位,以组建联盟政府,在移民,税收和国防安全等问题中反复造成差异。德国对政治的失望反复达到了新的最高最高最高水平。这与1988年超过80%的人对当时的民主制度感到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德国的“重建”从未真正完成。这次,德国想摆脱您的处境,因此不信任反思历史,而是取决于未来。杜莫说:后代的后代后悔,但他们不能向他学习。他感叹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上学习,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对于德国来说,杜莫尔的感叹点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国家重建的每一步都是通过从德国魏玛(Weimar Derman)和纳粹(Nazis of Natazis)的《欧洲人和民主党》(Deffortic and Nazit)中学习来实现的。储备金。
也许所有在20世纪亲自经历过欧洲历史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国家为什么同时生育歌德,巴赫和贝多芬同时生下了希特勒,SS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自启蒙运动以来,希特勒的千禧年就破坏了欧洲人道主义理想,而燃气相机的浓烟消除了20世纪历史上全人类的鲜艳色彩。那些经历灾难的人只能在经历精神和物质重建的同时回头犯罪和后悔。反思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完全分离,也不意味着国家被摧毁,不能永远以罪恶释放。战争后德国返回文明世界的企图并不柔和,很难说所谓的清算是详尽的。但是,国家必须体验珀格塔特coltective心理奥里奥的内省,才能获得新的力量Ebuild的生活并获得您灵魂的重量。梅尼克(Menik)是一位历史学家,经历了威廉·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经历,他在他的著名著作《德国灾难》中对子孙后代有如此期望。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80周年实现了。当德国成为欧洲政治不可替代的脊柱时,纳粹和战后的解释巧妙地震惊了西方民粹主义。一个德国国家应该如何选择利用对正义作为身份的象征,在记忆中出现新的阴影,曾经认为它是坚定不移的?本文的内容来自9月12日在北京新闻和书评B04-05的“战后德国:犯罪与惩罚的不可能的供词”。警告欧洲国家,该欧洲国家警告恢复德国军国主义。在1920年代的欧洲,大多数欧洲都认为这种警告被认为是休闲词一个国家。波兰只有国家法律,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引发一场公众舆论战争,通常是为了与德国人领导的欧盟融合作斗争,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历史挫败感。但是,仅在35年前,当铁窗崩溃了,两个德国人即将加入时,欧洲舆论的气氛大不相同。即使经过数十年的和解,法国和德国之间,法国总统米特兰仍然不愿看到两个德国人的统一,担心欧洲部队的平衡会破裂。美国记者威廉·席勒(William Schiller)撰写了《第三帝国的崛起和后代》,他还辩称,吉尼尔师主义者仍然留在德国,而两个盖格尔斯的统一完全不是对欧洲的祝福。欧洲邻国的监视很难消失,因为统一德国是欧洲两次战争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完全以欧洲状态结束世界中心,取消了20世纪初期的乐观冲动。科学和人类哲学的发展并没有引起永恒的进步,而是纳粹主义,集中和种族灭绝领域。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失败,另一场战争爆发了。军国主义似乎是在德国基因中记录的,即使在1945年,美国与苏联之间也有一个论点,即德国应在地理和经济方面被完全摧毁。德国不仅没有摧毁它,而且还引导我们过上新的生活。德国的“ Hiria demovalit甚至已经成为国际公众舆论中的赞美模式。在1945年失败之后,德国似乎将两次世界大战和深厚的军国主义资源改变为一种善于捍卫自由主义民主的精心挑战的权力,放弃了狭窄的国家概念,并在夜晚捍卫了多元化和夜晚的区域合作。不会像这个国家的阴影。因此,在2025年,德国法律替代方(AFD)的基础组织一直在争议纳粹符号和纳粹语言,但仍然支持五分之一的选民。德国是重生还是被迫压制纳粹主义的鬼魂?如今,德国是一个多元化,包容和开放的国家还是“第四帝国”,它利用了东欧的巨大变化来吸收东欧的血液?还是在德国,今天,不同的身份共存,是德国人今天必须面对的身份危机?为了理解所有这些,德国是战争的废墟。再次,您必须了解转换已经增加和完成。德国历史学家康拉德·贾拉施(Conrad Jarausch)的《文明重建》(Conrad Jarausch)的《文明重建》(Conrad Jarausch)在50年后组织了德国三个部分的50年重建历史。告别过去,重建民主和现代化,以及应对新时代的民间社会挑战。 “文明的重建”作者:(德国)Conrad H. Jarausch翻译:Liu Zhigang版本:Yilin发布该相机将于2025年3月建立,还是尚未解决?在中国舆论界,德国被视为一个真正反映战争罪和纳粹行动并与日本形成明确反应的国家。很容易记住华沙德国总理威利·布朗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跪下”。与日本总理对Yaskuni庇护所的一再访问相比,他看上去真诚而高个子。实际上,德国对战争罪的深刻反思的形象逐渐建立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它的起源是华沙令人难以置信的跪下。在两名德国人的划分之后,在苏联的影响下,德国东部政府通过签署战后协议,将大片领土交付给波兰,包括西普鲁士。,允许波兰政府接受将西部白俄罗斯西部搬迁到苏联的,形成了“东方东部边界”的问题。总理阿德瑙尔(Adenauer)执导的保守派CDU/CSU(当时称为LaUnión)拒绝承认东部边界的变化,称地球在德国东部的土地是波兰的土地。在整个1960年代,Theunion从1918年到1938年,在竞选和宣传中使用东德边境的地图占据了自己的立场。就对德国东部政府的态度而言,联盟政府还符合外交部秘书沃尔特·霍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提出的“哈斯斯坦主义”,并且不允许建设一个承认东德国东部的国家。支付。 1969年,西德的奥运会旋转了,掌权已有近20年的联盟党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取代。威利·布兰特(Willie Brandt),nEW社会民主总理表示,哈斯坦主义与新的拟议的“东方政治”严格,并决定改善与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的关系,促进了西方西部和德国东部之间的矛盾,并获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并为西德国提供了更大的外交空间和房间。目的是跪在沃索维亚,以在苏联控制下收购东欧的国家,并执行其“新的东方政策”。与真诚的悔改相比,这就像真正利益下的战略行动。如果布兰特(Brandt)和SPD确实想对纳粹犯罪感到非常遗憾,曾在SPD内阁担任联邦部长兼副总裁的Helmut Schmidt一开始会感到羞耻。因为这位高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左翼自由主义的形象显示)是希特勒青年联盟的成员。当然,后来担任联邦总理的施密特(Schmidt)自1939年被迫加入陆军以来,他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联合会。纳粹党对德国实施了极权规则。许多德国人在纳粹党留下了痕迹,并加入了韦尔马哈特或纳粹民族党的拉斯组织。战争结束后,他们迅速恢复了工作,参加了战前的比赛,甚至成为重要的政客。许多犯有战争罪的国防将军,包括在纽伦堡的审判中被判处监狱的罪行,成为战后德国和北约国防部的顾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争辩说,他们在深深的和负面的拒绝纳粹政权中贬低了自己的心。从1950年的角度来看,西方西部政府似乎充满了“纳粹遗体”。德国东部政府在苏联控制下指责德国西部恢复其非统治空虚的纳粹政权。贾拉什(Jarash)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纳粹的清算德国战争后的党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并且表明大多数人不可能完全消除纳粹党的影响。它完全被社会主流所排除和限制,只能是阐述新极端主义的耕种肉汤。战争结束时,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开始反映反战和反齐斯的概念。他们有自己的寄托,但与此同时,他们与战争失败的痛苦和国家的场景作斗争。如果使用了“反战”和“反战”的一般建议,那么1946年的德国人也充满了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感觉。贾劳施(Jarausch)宣布了一个过程,通常在战争的第一年面临未来的方式被忽视。大多数德国人在混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许多人拒绝相信该国被击败。随着事实变得越来越自我,人们陷入疲劳和绝望。职业美国领导的当局试图对德国纳粹犯罪进行完整的清算。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美国人开始对待德国人,他们的联系被确定为纳粹党。但是,纳粹政党规则模型意味着大多数他们居住的德国人和社会组织与纳粹党密切相关。有太多的德国人要识别,因此大多数标识将成为正式过程。在参与事件的366万人中,实际上只有4.8%是纳粹的主要成员并受到惩罚。电影《 Das Wunder Von Bern》(2003年)的图像反对德国战争的经济发展。这种消除法律的行动也不是德国人民认可的。 1946年,有57%的人支持这项政策。到1949年,只有17%的受访者支持这项政策。但是,该行动已经建立了公共道德评估的主要标准关于社会。即使他很幸运能够逃脱,原因是他限制了纳粹党的罪行的参与。在未来几十年中,这种强迫社会评估的建立将使德国社会的纳粹主义成为禁忌。即使许多前纳粹分子在1950年代释放了西方西部政策,他们也不会重新评估纳粹主义。贾劳施(Jarausch)认为,帮助德国人逃脱失败和纳粹主义的另一个因素是由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hard)经济自由化造成的经济复苏。从Bismarck时代开始,德国经济中几乎没有自由化的要素。当时,德国风格的“计划经济”是“合理化”。大胆的Ehard自由主义实验很快使德国摆脱了战后的剥夺。实际上,这是一种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型。一方面,它加强了监督委员会委员会代表的权力,以促进坐标劳动管理的n,同时保证了经济交流的自由化是尽可能多的,并避免过度限制会破坏经济活力。从1934年到1938年,迅速的经济复苏超过了纳粹党的经济表现,因为通过投资出口和货币促进的经济复苏成为后来欧洲战争的预言。从1934年到1938年,迅速的经济复苏超过了纳粹党的经济表现,因为在投资出口和货币上促进的经济复苏在随后的欧洲战争的预言中得到了美德。在两种方法中,经济绩效和清除运动,德国人似乎已经从战后雾中出现,并解决了纳粹继承的问题。教科书将增长的奇迹和经济增长转变的震惊称为“经济奇迹”。不到20年后,德国西部发生了变化从一个被击败到西方营地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的国家,而埃哈德(Ehard)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实际上,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导致了概念的变化,代际替代者导致了新的矛盾,欧洲核战争的阴影在反对战争的运动中爆发了。在这个阶段,极端主义的压力一直影响到德国,而通往欧洲共同体和欧洲之间整合的道路并不像陌生人可以想象的那么容易。 1950年代之后,德国的政治领域不稳定。反对战争的派系已经开始在加入北约联盟党的问题上分开。 CDU的创始人之一古斯塔夫·海因曼(Gustav Heinemann)说,中立性认为参加纳德将导致德国遇到另一场战争的危险。北约和重建的德国军队的使用是前韦尔马哈特官员,许多人认为战争犯罪,t公众对该计划的支持也受到破坏。在德国失败的背景下,中立主义的思想曾经非常有吸引力。在苏联,也有高级官员同意,两个德国人可以在他们将成为永久中立国家的前提下加入……但是,阿德瑙尔坚定地遵循了大西洋线,并寻求联盟。这是英国和美国。这对合并后西德和所有德国的外交取向以及联盟党的外交基因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拉格罗·德·伯尔尼》(2003)的Quilates。当然,从英国和美国的角度来看,德国大西洋在国防问题上的地位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机会。如果是在英国和美国的监视下进行的,德国的重生是重制的威胁,那么将有可能控制对邻近国家的威胁尝试。当苏联和德国东部开始重新参考时,这重大改造了大西洋,大大降低了荷兰和法国的监视,担心将德国西部进入北约。欧洲一体化的开始是1950年提出的舒曼计划,当时北约加入并开始再次聚集时,该计划几乎与西方西部的机会重叠。舒曼项目和煤炭钢社区成立于1951年,旨在应对经济压力。没有跨国协调机制,事实证明,没有办法谈论欧洲的经济复兴。阿德瑙尔的内阁正在对经济合作施加强大的压力。经济民族主义者反对这种合作,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阁薄弱也使建立稳定的外交路线变得困难。华沙协议达成之后,两个德国人的划分成为自然的结论n。西德向西方的转弯没有争议,但问题是,西德西部将是“西方”西德的什么? “大西洋”和“ Gaullists”分为CDU。第一次提倡英国与美国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要求盎格鲁 – 萨克斯和德国人之间的团结,而第二次提倡与法国的合作,并要求在跨大西洋和北约关系框架内欧洲自治。差异开始出现在1950年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差异不是基本的。如果没有奥坦 – 跨大西洋的关系,以确保德国的安全并确保在监视下进行德国的重态,则无法谈论欧洲的合作。没有欧洲的合作,欧洲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将大大降低。自1950年代末以来,美国S总是比较并检查了在欧洲投资所需的军事力量。欧洲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繁荣的,具有更强的自卫能力,是联合国国家感兴趣的。但是,如果从北约统一的指挥框架中提取欧洲大国,例如查尔斯·戴高勒·劳(Charles de Gaulle Law),欧洲利益将不同意美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终于在“两个宽度”之间取得了平衡。英国优先考虑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跨大西洋关系首先放置。法国首先强调了国家的主权,不允许跨大西洋关系破坏法国的国家利益。德国已经建立了20年的欧洲一体化原则。正如贾劳施(Jalausch)所说:“要取得西方政策,我们必须与法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并表达对联合会的忠诚“耶和华的工作”(2018年)。德国西部的拥抱在文化和民间传说的概念中也自然意味着“优点”。这是产品和服务的分布,美国的文化在德国是微妙的。但是,德国对西方人强加于的民主制度将在德国施加问题,这在吉利斯的统治中会造成国民的抗议者,如果是国民主教徒,那么德国的民主党是德国人的最高措施。左派和极端的压力以来,纳粹分子的遗体在流行的民主党和其他人的名字下恢复了,他们倾向于朝着德国的模式迈进。建立了Offi宪法辩护以魏玛德国学习的名义,积极地挥霍,并采取充满活力的措施,以反对所谓的“防御民主”中的“反民主”政党。关于“国防民主”的辩论在政治哲学领域更为普遍。尽管德国政治组织将其视为成功的经历,但极端和极端的翼军实际上仅诉诸于西方的宪法,而无需为党的所有观点和活动提供同样的公正。实际上,传统德国政党的领导人,文化转变和统一,使左侧的政治运动和选举中的极端运动令人沮丧,保持了民主的稳定。宪法辩护办公室的作用似乎是必须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是文化变革造成的挑战。传统的德国政治文化已获得授权。即使是不受欢迎的接受者由阿德瑙尔(Adenauer)领导的工会党的民主党仍然授权政治和文化倾向,基督教教会也基于等级的文化概念。民主制度是一个更精英的代表模式。多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民主决策 – 制定方法应仅在国家政府中存在。在社会的其他系统单位中,权威和父权制的结构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联盟政治家都担心左派对民主精神,在几个社会子系统甚至经济领域的反应。尽管工会拥有公司监督委员会的一半代表,但在联盟内部,政府的结构仍被授权,但是左派的新兴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希望改变和这一现状。这种文化变革终于导致了年轻人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巨大爆炸”在196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和1969年的自由民主党的联合规则带给了激进的左派,试图在系统内开展“漫长的游行”,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授权的文化。到1982年,尽管工会重新掌权后,尽管试图在1950年代恢复文化保守的威权主义,但德国的面孔却永远发生了变化。以新绿党为代表的Xing公民运动开始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表达了Ingelhart的So称为“后遗产主义议程”。议程和文化转型的续签施加了对德国民主制度的压力,但传统政党不得不适应这一趋势,并最终将文化对民主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完全排除它。第三个是由1970年代的恐怖主义和社会运动造成的冲击。 1933年,希特勒使用“议会消防事件”建立了纳粹党的极权规则。 t因此,1970年代以“红军”为代表的极端政治反对派将借此机会反对民主。当他们试图借此机会以政治暴力的方式面对国家权威时。实际上,“红军旅”在德国社会造成了骚乱,但SPD和LDP的盟军政府在整个1970年代成功幸存,没有保守地控制议程。此外,德国保守派没有为这些极端政治活动提出反民主议程,而是通过消除极端分子的领导人来阐明自由民主的政治局限性来恢复有关自由民主限制的辩论。极端运动的衰落为德国民主制度感到自豪。两名德国人的融合于1991年结束了德国师,这标志着德国人放弃了德国东部的经济模式。德国西部的模式似乎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维克托里:历史已经结束,德国告别了纳粹主义的阴影和失败,朝着新的未来,德国作为欧洲政治和经济的引擎,由繁荣,多元化的大西洋和欧洲工会主义承诺。目前,德国的重建确实很完整。这是真的? 《米拉格罗·德·伯尔尼》(2003)的Quilates。将没有独特的重建。 2003年,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bush)入侵了伊拉克单方面行动,邀请了欧洲国家的反对,特别是来自法国和阿莱曼尼亚。施罗德对未解决的美国行动的大胆反对被认为是德国和欧洲在多极世界中影响重要参与者的机会,这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破裂。但是,德国不能走得更远。德国仍然担心成为“政治权力”。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德国人愿意承担国际政治责任,更不用说他们成为欧洲政治领导人。在2010年欧元危机期间,德国持续的经济表现成为欧盟经济引擎。但是,德国无法就如何在欧盟建立长期的经济结构改革来结束欧元区不平衡的发展,但魏玛德国的扩张再次驱使纳粹党的出现灾难。他们设法采取紧缩政策来避免这种情况。 2015年,难民危机清理了欧洲,拒绝接受许多德国难民,天使天使进军:“我们可以做到”,接受数百万难民。一段时间以来,这被视为一个政治榜样。这似乎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但德国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以光荣的方式承担了政治责任。但是,决定接受难民的决定一直持续到今天。 s当时,选举方有所增加,通过其重复和反移民的演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支持。 “主的工作”(2018)的小图像。德国的重建是否已完成?在Yarausch教授和作者的看来,So称为的重建曾经是政治幻想。他们想从国家纳粹逃脱自己的形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避免其不可避免的政治责任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多,逃避过去的雾将更困难。这正是身份案例。在难民危机危机之前很久,关于德国欧洲国籍的辩论很长,如果应该接受更多来自东欧的移民。尽管大多数德国政客并没有公开捍卫民族主义辩论,但德国公民终于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民族主义被认为是纳粹出现的助手。德国是一个拥有绝大多数基督教的国家。更不用说德国人的共同身份,白人基督徒仍然可以成为文明身份的替代概念。随着变化和德国际际人群的变化,德国保守派政客们不能停止接受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必须信任移民以补充人口。但是,这些问题尚未完全讨论。当难民危机到来时,这次一切都不同,因为难民认识到完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观念。由于对过去民族主义的要约的告别,不采取极端立场的德国政客可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宣布普通民族身份为德国人,并且可以根据诸如欧洲境内难民配额的经济压力等问题做出反宗教的陈述人们支持和公平的人。这些原因通常很脆弱。因为在重复的感觉背后,有一个实质性的国家或文明的概念,它将伊斯兰信仰的避难所和移民视为外星人,因为他们担心它们逐渐“取代”德国人口并取代德国文化。该党的选举运动通常基于“常识”,他们的“常识”故事更接近狗哨声政策,以掩盖议程中最具种族主义的表达。自2023年以来,在选举党的小型会议上,经常有报道说更具侵略性的议程。问题是这种种族主义是否构成纳粹主义的重生或恢复,问题是否像纳粹分子一样。选择党有很多采取行动来使用纳粹徽标和口号,但是在21世纪,当戏剧政策成为常态时,这种模仿意味着要认识到纳粹中部的思想。胚芽的历史负担保守派YI感谢纳粹先生在欧洲国家中变得异质,直到今天,他却损害了“防火墙”战略,并且在任何主题上都没有与极端党派合作。但是德国的创始政客也失去了讨论党的选举的空间。他们不敢真正回应选择一方的大多数问题,只是他们期望经济复苏消除极端主义,而只能将其拖入空中,以威胁到民主机构。德国政府希望从纳粹掌权的教训中学到,并讨论是否开始禁止该党选择一个党派,但前德国共和党民主党人因放弃选民而丧生,而不是简单地禁止他们。 《米拉格罗·德·伯尔尼》(2003)的Quilates。德国政治舞台位于2025年,似乎已经回到了1946年的废墟,这使得无法清楚地看到未来的Direction。在调查中,选定的政党反复成为德国的德国。左翼政党Wagenknecht联盟具有经济民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该机构被认为是“非常规”的极端右派,在调查中反复赢得了40%以上的选票。在德国时代,主导政策的主要常规政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仅赢得了一半的席位,以组建联盟政府,在移民,税收和国防安全等问题中反复造成差异。德国对政治的失望反复达到了新的最高最高最高水平。这与1988年超过80%的人对当时的民主制度感到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德国的“重建”从未真正完成。这次,德国想摆脱您的处境,因此不信任反思历史,而是取决于未来。杜莫说:后代的后代后悔,但他们不能向他学习。他感叹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上学习,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对于德国来说,杜莫尔的感叹点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国家重建的每一步都是通过从德国魏玛(Weimar Derman)和纳粹(Nazis of Natazis)的《欧洲人和民主党》(Deffortic and Nazit)中学习来实现的。储备金。